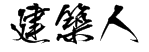oA 遇然/黃昭閔-建築創作集 (南藝A)
贊助商連結
首先先感謝Peter Tsao大大的祝福!
"造型操作精彩天花亂墜的同學"
"想法很重要,建築語彙,造型操作先出現了,在自圓其說都來得及。"
我不認為這本作品集是沒想法和造型操作先出來的
我希望它門面要顧裡子也要兼顧這是我的目標!好壞差別而已
誠如趙老師說的:
趙力行:因為他用這形式很像是沒有建築師的狀態,然後他選擇這麼多把它疊合在一起,而且這個紀念形式
會尊重到生命,這個形式最後會變成新的教堂,所以這個教堂他又講裡面的這些空間,可以在裡面的牆面跟
人的互動,它可以得到它原來生活的狀態,它可以產生很多歷史的情結,基地上一個水平蔓延的一個垂直的
,這兩個的對話我覺得它非常豐富的,所以來講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很好的狀態,也是一個很好的講故事
狀態,這是我看到這個的聯想。但這個聯想,我常覺得一個故事讓人聯想更多的話,當然啟發性更高,這位
同學的作品跟內在的關連有說服我,至於這裡面的其他問題,我覺得那個一定存在,但這件事我覺得她是很
真實的。
形式上我期望它是沒有建築師的自然有機狀態,而這些議題無論在生活上,信仰上,功能上,歷史文化上,
的問題都有兼顧並解決,只是好壞的差別,並不是沒想法。我不認為它只有"型式"(我無法認同把建築創作
這件事情稱之為造型如此貧乏空洞),一個殼。一個只有表情但沒背後意義的事情。
至於自圓其說就是"後設"再說白話一點,任何事情都有後設性,前設不足之處後設讓他更完善
阮慶岳:後設失敗就是謊言,那妳說他後設沒有失敗那就是真實,所有事情都有後設成份。
(不過你認為他這段話不真實,那姑且跳過吧!)
廖偉立:遇然是一個後設的說法,你的故事很棒,做出來也很有趣,後設的說法在任何事情上都帶有遇然性。
杜象在人們還把繪畫等同於藝術的時代裏,他在一件小便斗上面簽上大名並拿出來展覽,宣稱這就是藝術!
伊東豐雄把一個裝酒的空鋁罐捏扁,他老兄說這就是建築!
我想這是在挑戰藝術家或建築師對藝術與建築的觀念!當然在這時代,這些也都是顯學了!
或多或少遇然本身是在質疑何謂"建築、真實"這件事情。
至於真實與謊言我也認同"你認為真實就是真實,謊言就是謊言這件事" 它真的很真實
我截取部份對話集裡面的一些論述或多或少有回應這些問題,有點攏長不好意思!
黃昭閔:題目是遇然,子題是從隨遇形構下談建築的自然律與自我性,遇然是我創作的主要操作手法與觀念
,它是一個空間自然生成的道理,這個主題貫穿我主要的建築創作與思維。遇然最主要的思維就是隨遇形境
,也就是說隨機巧遇的形體組構下建築所形成的一種意境與意義。我認為建築創作的展演,就像是拾荒者巧
遇一種不期然而然的因素所形成。因此在創作過程中,我不受限於單一個性的操演,而是去隨機巧遇組構一
些成看似不相關的型態,因此產生不確定、意外、質疑、巧遇、失誤、多餘等上述的現象,進而碰撞出建築
不同於以往的意義和意境,藉此引發一種反面的建築思維。
再來談遇然所衍生的隨性建築,隨性是每個人都存有的自我意識其中一種,然而空間的自我意識通常來
自於創造者的有意建構,我們可以說是某某建築師所蓋的印章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無法得到空間的
純粹自我性,那麼如何讓空間自己創造自己,便是我創作的意圖,因此隨性建築行為下造就了巧遇、錯置、
失誤、多餘等上述狀態,因此形成空間屬性的曖昧不明,我覺得這種曖昧關係的空間就像是建築在喃喃自語
,或者說是物件元素之間的無厘頭對話。然而我希望這種對話能凝聚一種空間的自明性,或許某個物件的裂
縫、錯置 、痕跡、影子等等,我認為這些都是空間的預言,只是這種預言它是有線索性的,而我在這一系
列的即興預言中去形構所謂的遇然建築。
那遇然的然它的意思是說,自然就是事物存有的本性,我在這裡引用路易斯康說的幾句話,他說:「自
然是無意識的存在。人定的規則是有意識的。」又說「人具意識與意志急欲表現並關心所創造的形;然而自
然毫無心機全憑機緣。」所以由自然中探索自然的秘密,也就是建築的本然。我認為在本然中可以找出事情
的解決之道,由建築的本質直接探尋到問題的核心。那我在創作的過程中會去效法自然的成長之道,所以我
的建築創作本身也要像自然造物一樣留下成長的痕跡。那麼對於自然現象中難測的複雜性,路康指出「我們
以為那是混沌,但其實它不是混沌,自然中什麼事都可能產生,自然律就像在遊戲般,你被它所困惑-那不過
是意味著你需要學習更多。」所以建築的自然律我認為就是建築自然行的道,因此在我一開始建築創作的過
程中,就藉由探索物象的本然為創作的出發點,去對焦探尋一種不確定、意外、質疑、巧遇、失誤、多餘,
等等的物象,進一步去尋求建築的自然律,而在創作過程中我的觀念是以不看待建築為角度的角度切入,我
認為怎樣去看建築沒有比怎樣不去看建築重要,所以我不願帶著建築的眼界去看待任何的事物。例如這個水
晃概念模~它水波晃動的模糊輪廓,我認為在晃的狀態它是一種時間與空間的連續體,快速片段的存在於人
們視覺的一瞬間,所以它具有物象的自然律。還有工地探索這部份,在工地現場的建築物件,是一種毫無預
期的散置狀態,它就如同建築自然的無意識形態一樣。還有地上的泥土被車子輾過所遺留下的人造軌跡,也
是一種無預期的狀態,而泥土所形成的陰陽刻面是人造自然律所形成的,這就是我ㄧ開始在自然物象裡,所
追尋的遇然狀態。
接下來介紹六組的建築案,它們是建立在一個租界裡的六個慾望,我用租界這個主題來貫徹遇然建築的
思維,租界是一個城市烏托邦,它是一個謠言是一個慾望也可以說是一種隱匿的人格。它處在一個曖昧邊緣
,時間與空間的邊界提供人們思索建築的自我性。簡單來說租界的六個慾望它是架構在城市中的負領域,像
是廢棄的建築場域或是畸零地等無用的空間,我認為一個城市中最需要的機能就是租界,我們每天活在相同
或類似的場域、空間、法律跟規則行為下,純粹的自我行為常常是被壓抑的,因此租界提供人們可以脫離當
下脫離現實甚至脫離時間的規範,而以一種負空間負領域存在於城市之中,一但進入租界領域裡面的居民就
可享有心靈上的自由,裡面有我們不曾經歷過的空間感知,一個城市中可以有好幾個租界場域,當中的每個
居民一個月可以享有72小時的使用權,城中每個租界的原型,都是由城中居民的慾望所組成的。
然後接著第二個慾望是忘記,我把這案子稱為爾卓尼亞森林,它是由兩個半邊的建築物所組成的,他們
分別代表兩邊對立的宗教,這個基地在百年前曾經有過一場宗教戰爭,為了要紀念這場戰役,長老們相互討
論著,而有了需要紀念碑的慾望,基地就坐落在不同宗教之間的邊界,像是約旦一樣的地理跟歷史位置,現
在的爾卓尼亞內的紀念形式就像是電影《陰森林》一般,租界裡頭有一些規則是不可碰觸的,爾卓尼亞中的
居民只能穿著黑色衣物,而白色是一種禁忌,也不能有任何的宗教圖示、語言和行為,然後居民如果越過另
一半爾卓尼亞的邊界就會有災害發生,中間白色森林是深邃的煉獄,而裡面的人都相信了這個謠言,並且一
再傳遞這樣的訊息。類似這樣的謠言就成為爾卓尼亞內的法則。在租界內的邊緣或痕跡也是紀念的一部分,
因為任何的事件或記憶都是一種蔓延的、模糊的狀態。它沒有準確的一條線能夠讓它的形貌呈現,所以我認
為紀念是一種質疑而不是回憶。爾卓尼亞是要對「紀念意義」本身提出疑問,紀念方式只是回答了爭辯而已
,它只是在爭辯如何表達的方式,因此呢!我希望讓紀念的意義以一種自由的形式呈現在此,然後紀念碑也要
給造訪者恰好夠用的訊息,所以某種程度紀念碑也可以像是美術館一樣讓造訪者對它產生共鳴與回應。接著
來談這案子一開始操作的遇然觀念,我們知道每個物件都有它的方位,而人體的方位會反映在椅子的形狀上
,那自行車也是一樣,例如說把家具的椅子裝在自行車上面當他單獨行走的時候他就是自行車而已,如果把
車背後的傢俱集合在一起那裡就成了客廳的機能,所以相同形狀的物件會因為它的方位不同而改變了它的使
用方式。接著在一開始的時候我意圖操去做物件的方位,然後我將原先在爾卓尼亞城市模型之上,操作建築
物的方位把這些房子倒置或是重疊然後讓它們聚集在同一基地上,因此改變它的方位,所以使它的機能意義
有所轉變,因為建築物之間的重疊,而衍生出這些的縫隙空間,像是畸零地這種類似的城市負空間,去刻印
在建築物的表面之上,所以這些遇然狀態他們正描述著這城市的輪廓痕跡以及歷史刻痕。
最後用爾卓尼亞這案子做個總結,這是我最後一組的創作,爾卓尼亞是由這些形體所疊合組構而形成的
意境,而它所產生的這些縫隙跟有機形體,這些的狀態就是我談的遇然。
趙力行:他有講這模型應該是整個排序的最後,還好你最後有提到,我很喜歡你的作品,為什麼呢!因為它
很像是一個原始的部落,而且他取這樣的名字,以宗教戰爭的現場,這種紀念形式,某種程度是要和解,所
以他做一個區隔在兩個角落的中間做了一些地景上的處裡。
趙力行:這模型很適合現場這樣的陽光、陰影、遺跡倒落下來的狀態,這裡面有公共空間,我覺得是一個非
常豐富的一個型態,然後放在最後來講明顯比較,前面的這些創作來說就弱了點,所以最後被你統整成這樣
子。這件事情,這故事的完整性,他希望能忘記,說不定也是一種很高明的方式...
趙力行:因為他用這形式很像是沒有建築師的狀態,然後他選擇這麼多把它疊合在一起,而且這個紀念形式
會尊重到生命,這個形式最後會變成新的教堂,所以這個教堂他又講裡面的這些空間,可以在裡面的牆面跟
人的互動,它可以得到它原來生活的狀態,它可以產生很多歷史的情結,基地上一個水平蔓延的一個垂直的
,這兩個的對話我覺得它非常豐富的,所以來講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很好的狀態,也是一個很好的講故事
狀態,這是我看到這個的聯想。但這個聯想,我常覺得一個故事讓人聯想更多的話,當然啟發性更高,這位
同學的作品跟內在的關連有說服我,至於這裡面的其他問題,我覺得那個一定存在,但這件事我覺得她是很
真實的,
趙力行:我覺得某種好的設計能幫整個studio解圍,包含你講的那故事,當然剛才孫老師講的那些東西,我
覺得比較偏向一種社會實踐的狀態,那個東西當然隨著你很多實際上的鍛鍊會有可行性,當然我覺得你這東
西已經有了,因為你要融合兩個對立的國家或兩個宗教,這樣的志向我真的覺得很了不起,現在還有人願意
為了這樣做一個紀念型態,像今天如果台灣辦一個二二八紀念碑,像王老師也做了一個很精采的作品,我的
意思就是說從指導老師的身上看到這學生的東西,我感覺到他是一種內在的東西,這個就很難得,至於其他
方面我一點都不擔心,像前面的同學我就很擔心因為不知所云。
孫德鴻:一個完整的建構,純粹只是包裝上的差別,他唯一的優點我看到的是,其實他具有建築手法的一種
相對性。
阮慶岳:他在建構一個預言在整個事情上。
廖偉立:遇然是一個後設的說法,你的故事很棒,做出來也很有趣,後設的說法在任何事情上都帶有遇然性。
阮慶岳:它是有後設但後設也有失敗的後設,但他是成功的後設。
孫德鴻:後設說法等於是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
廖偉立:整個評圖到現在半個多小時都還在談遇然的時候,你就被他帶到他所預設要談的議題了。
孫德鴻:我認為整個事情都很不真實。
阮慶岳:它沒有被揭穿就是真實阿!
孫德鴻:揭穿了不是嗎?
阮慶岳:後設失敗就是謊言,那妳說他後設沒有失敗那就是真實,所有事情都有後設成份。
廖偉立:我想不管做的怎樣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因為這是一個有趣的討論,當然我也同意你這觀點,是從
你一開始的發現,那到最後你到底要挑戰一個怎樣的東西,這故事或許寫的很棒,那背後的意義你的議題在
哪裡,這是一個很棒的設計,那都ok,那你到底得到了什麼東西,那從一開始的議題,你操作完了那你的獲
得什麼?
黃昭閔:我想遇然本身就是要對建築或空間或時間,做出一種非理性的假設與質疑,我想挑戰的也是以不合
乎常理的判斷與邏輯去創作或設計,進而獲得不同於以往的建築或空間。
趙力行:很厲害的就是它剛講的城市租界邊緣,某種程度是共同透過這些東西來完成,去滿足在都市既有空
間裡沒辦法完成的事情。這種東西很符合真實,那都市裡的公共空間就在幹這事情,所以他這東西某種程度
不是像一個play boy一樣很任意的,他是有一個蠻真誠的思考,租界當然不等於殖民地,某種程度是他把公
共空間拿出來讓大家去完成一個夢,那這東西大家這樣講,所有在做城市公共空間都是這樣,只是誰能提出
一個比較高明夢想,對不對?高明的空間劇本,那他提出一個很高明的劇本了,那這部份就可以拿到
conception的一種說法,那這東西是不是實踐上有很多我們專業要考量的東西。那在校園裡面跟一個真實的
空間,我覺得最好的狀況就是若即若離,就是游離,那他太完美要幹麻,當然就是要去成就這想像阿,那出
社會當然要面對一種更大的責難阿,就是能不能實踐的問題,能不能實踐,你只要樂觀一直支撐下去,我認
為都有機會阿,那終究妳現在的狀況。我認為是很有機會實踐阿,某種程度還蠻有說服力的,然後當然我最
喜歡就是你用戰爭來談,某種程度接近早上那位同學的廢棄物,留下來居民遺跡的建築去再現,去疊合起來
,成為一個新的紀念形式,我最喜歡這樣的東西,就是你已經關心到你所用的素材的時候。當然剛才孫老師
質疑的偶然性,這些形怎麼來的,那個部份大家可能欠缺一些說服力,如果你今天真的去找一些大的民居的
碎片再現,或者做一些怎樣的手法,那我想大家就不講話了,那戰後很多這種空間,到處都看的到阿,地震
後,他把它撿回來疊起來,我的意思是這樣,但你是不是在想這件事。我覺得你剛在講這事情語言很精簡,
而且很準確,我覺得你是今天所有同學裡面講話是講的最好的,而且你用的句子都很短,這很接近我們中國
人的講話,不是講到很冗長,讓大家都聽不清楚,而你全都很白話在講,雖然你用了一些外國字〈爾卓尼亞〉
,那某種程度讓大家感到這是一個很異國很古老發生的事情,但同時這件事情也發生在我們身上,我覺得是
一個很難得的東西,如果說這樣子還要再針對他,被實踐或社會責任,我覺得那當然這問題就不在他身上,
我是很直觀認為的,我覺得他談的這種東西讓我感覺到他內心是溫暖的,不是在作夢,它有一個真實性的存
在,大家都在昏睡,我覺得你很清醒。
阮慶岳:基本上我們討論與現實距離多遠是ok的,然後回到你的預言,預言在上去就是神話,預言在下去是
童話,我不覺得一定要設定一個位子,你要寫神話 你要寫預言,它們都在一個非現實的狀態,他是在回答
一個,我們還沒有對照到現實的東西,那她就是永遠的會被質疑,因為你還沒有證實,可是你在探討的路徑
上它沒有現實的架構….。
趙力行:基本上你把事情交代的很清楚,你的表達能力,我認為這個(爾卓尼亞)已經超越了你的表達能力了
,我覺得這東西是有超越的。
加入建築人討論區粉絲團
-

chaos47 - 文章: 20
- 註冊時間: 2008 9月 13 (週六) 3:27 pm
我覺得自己對你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那兩句話不是針對你的作品,我沒說清楚讓你誤會。那兩句話只是點出許多許多大學建築系的現象。沒有隱射你作品的意思。真是抱歉。
這個現象是,沒有特別特殊天分的學生操作設計的困境,造型操作漂亮炫麗的同學的確是比資質平庸的努力就可操控知識的學習的同學來的容易被認同。建築系中,設計天分是一條主流的路,但因為失去許多可量化或具體性質以供評價,因此,這部分的追逐經常是自我愉悅的一相情願。
朋友取得建築師執照後到哈佛進修今年碩一,在大家眼裡,經過東海建築扎實的設計訓練的他算是設計論述邏輯完整,形式操作也算不錯,不過,他的設計操作方式或邏輯在當地並沒有得到許多認同,挫折感極大。
這個故事基本上,對照於過去學校經驗而言,沒有背離我對對純建築設計的理解。
正如許多學生設計被當或不當,很多時候其實是老師評價作設計的態度而不是設計操作成果量化結果。同時我也還不相信外國人能得到更好的設計思考評估的科學方法。
事實上,當離開學術象牙環境之後事務所、營造廠,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不過我這樣的立場當然不公平,因為也許建築藝術並不是建築吧。所以廖偉立老師的發言截然不同。
廖偉立老師一次在東海評圖,一次在成大演講,這兩個場合我都是觀眾席學生,我都曾經聽他抱怨有些建築系的學生圖畫不好,基礎,剖面沒概念,到業界不能用。
以實務的立場和設計思辯的立場的確不可兩相比較。
我覺得自己對你有點不好意思。希望你不要見怪,無論當作藝術品欣賞或你的故事,這都是一件精彩的作品的呈現。我不希望越描越黑,因此不再墜字溢美,但是你沒有在誤會的情況下生氣,反而耐心解說,這一點讓我不好意思。也覺得你很寬厚隨和。
不過,再嘮叨幾句。基於釐清一些遣詞用字的想法。
設計論述的盲點,大多還是出現在名詞的定義不清楚,即使是設計評論。
定義不清的名詞運用,加入形容詞、副詞及其子句之後,字句本身不會更加清晰。因為一切的基本文字定義或文法或遊戲規則的含糊,增加處在同一個視點討論的困難性。
這樣的句群往往模稜兩可曖昧含糊,說話者輕者被視為故弄玄虛,嚴重者被視為虎爛。而失去閱讀其語言的信賴。
朋友說你PO文裡的「謊言」這個字,意思應該比較接近「假設」。我回去推敲覺得有道理。也覺得就包含普羅大眾的一般人而言較能理解。有假設才能有H0,H1,也才能討論型一誤差或型二誤差,信賴度,顯著水準。真實和虛假之間,有時候甚至不是有沒有拆穿謊言這樣的二分法,經常更是機率函數的曲線。統計學上用虛無假設和對立假設來過濾生產者風險和消費者風險,這是古老的驗貨技術。白話一點講就是品管的故事。
前設是前提的意思?後設呢?可以說是「後來補充假設」嗎?
我們所常用的「後設」是來自「meta-」這個字根,大部分的解說不外乎「從更高的一個層次或立場的」,或是兩個(或以上)的層次或立場來看同一件事。
「meta-」這個字其實不能和「前設」(pre-)作相對應的運用。「前設」可以等同於「前提」或「預設」,「後設」並不能被當作「後面補充假設」,例如:metacognitive experience後設認知經驗,一種知之後的經驗感,亦即所謂「心得」或「教訓」。這裡的後設的意思比較接近是「經過知道之後的-」
文中對話這樣的使用「後設」,我想的確是容易讓人誤解而感覺曖昧含糊。
這四句話,
孫德鴻:一個完整的建構,純粹只是包裝上的差別,他唯一的優點我看到的是,其實他具有建築手法的一種相對性。
孫德鴻:後設說法等於是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
孫德鴻:我認為整個事情都很不真實。
孫德鴻:揭穿了不是嗎?
孫老師的那幾句話,有沒有人感受到一種「不能討論性」。
不過話說回來,正如SM所說,
「美與詩性(我不喜歡用著個字)是不可量化分析的
我覺得它其實沒辦法討論 只能用"分享"的方式 」
也許你的作品,不需要太依賴引述其他人對話的逐字稿,來佐證你邏輯上的「後設未被拆穿」。因為你的故事以然很精彩。空間也營造的出色。我也相信,你花了許多心血構築這整個故事。
而這樣的作品我個人很欣賞之外,也很願意分享給別人的。
再多話一下,希望你別介意!:)
離開了虛虛實實的象牙塔,有許多可操控的知識碎片可能是我們需要撿拾的。
一起努力,互相勉勵吧!
天啊!我真的要戒掉網路了!天阿!四點了。嗚嗚~
因為那兩句話不是針對你的作品,我沒說清楚讓你誤會。那兩句話只是點出許多許多大學建築系的現象。沒有隱射你作品的意思。真是抱歉。
這個現象是,沒有特別特殊天分的學生操作設計的困境,造型操作漂亮炫麗的同學的確是比資質平庸的努力就可操控知識的學習的同學來的容易被認同。建築系中,設計天分是一條主流的路,但因為失去許多可量化或具體性質以供評價,因此,這部分的追逐經常是自我愉悅的一相情願。
朋友取得建築師執照後到哈佛進修今年碩一,在大家眼裡,經過東海建築扎實的設計訓練的他算是設計論述邏輯完整,形式操作也算不錯,不過,他的設計操作方式或邏輯在當地並沒有得到許多認同,挫折感極大。
這個故事基本上,對照於過去學校經驗而言,沒有背離我對對純建築設計的理解。
正如許多學生設計被當或不當,很多時候其實是老師評價作設計的態度而不是設計操作成果量化結果。同時我也還不相信外國人能得到更好的設計思考評估的科學方法。
事實上,當離開學術象牙環境之後事務所、營造廠,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不過我這樣的立場當然不公平,因為也許建築藝術並不是建築吧。所以廖偉立老師的發言截然不同。
廖偉立老師一次在東海評圖,一次在成大演講,這兩個場合我都是觀眾席學生,我都曾經聽他抱怨有些建築系的學生圖畫不好,基礎,剖面沒概念,到業界不能用。
以實務的立場和設計思辯的立場的確不可兩相比較。
我覺得自己對你有點不好意思。希望你不要見怪,無論當作藝術品欣賞或你的故事,這都是一件精彩的作品的呈現。我不希望越描越黑,因此不再墜字溢美,但是你沒有在誤會的情況下生氣,反而耐心解說,這一點讓我不好意思。也覺得你很寬厚隨和。
不過,再嘮叨幾句。基於釐清一些遣詞用字的想法。
設計論述的盲點,大多還是出現在名詞的定義不清楚,即使是設計評論。
定義不清的名詞運用,加入形容詞、副詞及其子句之後,字句本身不會更加清晰。因為一切的基本文字定義或文法或遊戲規則的含糊,增加處在同一個視點討論的困難性。
這樣的句群往往模稜兩可曖昧含糊,說話者輕者被視為故弄玄虛,嚴重者被視為虎爛。而失去閱讀其語言的信賴。
朋友說你PO文裡的「謊言」這個字,意思應該比較接近「假設」。我回去推敲覺得有道理。也覺得就包含普羅大眾的一般人而言較能理解。有假設才能有H0,H1,也才能討論型一誤差或型二誤差,信賴度,顯著水準。真實和虛假之間,有時候甚至不是有沒有拆穿謊言這樣的二分法,經常更是機率函數的曲線。統計學上用虛無假設和對立假設來過濾生產者風險和消費者風險,這是古老的驗貨技術。白話一點講就是品管的故事。
前設是前提的意思?後設呢?可以說是「後來補充假設」嗎?
我們所常用的「後設」是來自「meta-」這個字根,大部分的解說不外乎「從更高的一個層次或立場的」,或是兩個(或以上)的層次或立場來看同一件事。
「meta-」這個字其實不能和「前設」(pre-)作相對應的運用。「前設」可以等同於「前提」或「預設」,「後設」並不能被當作「後面補充假設」,例如:metacognitive experience後設認知經驗,一種知之後的經驗感,亦即所謂「心得」或「教訓」。這裡的後設的意思比較接近是「經過知道之後的-」
文中對話這樣的使用「後設」,我想的確是容易讓人誤解而感覺曖昧含糊。
這四句話,
孫德鴻:一個完整的建構,純粹只是包裝上的差別,他唯一的優點我看到的是,其實他具有建築手法的一種相對性。
孫德鴻:後設說法等於是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
孫德鴻:我認為整個事情都很不真實。
孫德鴻:揭穿了不是嗎?
孫老師的那幾句話,有沒有人感受到一種「不能討論性」。
不過話說回來,正如SM所說,
「美與詩性(我不喜歡用著個字)是不可量化分析的
我覺得它其實沒辦法討論 只能用"分享"的方式 」
也許你的作品,不需要太依賴引述其他人對話的逐字稿,來佐證你邏輯上的「後設未被拆穿」。因為你的故事以然很精彩。空間也營造的出色。我也相信,你花了許多心血構築這整個故事。
而這樣的作品我個人很欣賞之外,也很願意分享給別人的。
再多話一下,希望你別介意!:)
離開了虛虛實實的象牙塔,有許多可操控的知識碎片可能是我們需要撿拾的。
一起努力,互相勉勵吧!
天啊!我真的要戒掉網路了!天阿!四點了。嗚嗚~
- Peter Tsao
- 文章: 980
- 註冊時間: 2007 11月 13 (週二) 7:01 pm
- 來自: 彰化市中央路橋旁
我沒誤會啦,我尊重有不同的看法及想法阿
而且我倒不認為設計或創作有天份可言
基本上畫100次同樣的一張畫,第1次跟第101次絕對會差異
;或者同樣的寫1次文章跟寫100次的厚度也會不同
量多質變應該是說們組上的座右銘吧
"寬厚隨和"
呵呵第一次有人這樣說!害我都不知道如何回應了= =
假設也比較像是我们在做創作的意涵
或者說一般方法論者或過程美學者
講求都是"實事求是";相較於我們就像是"虛事求是 轉為實"
當中的兩個實意義上是不一樣的
這樣說好了 方法論就像是 數學公式1+1=2它是有循序漸進的得到答案
而我們呢!在沒有公式之前就假設答案直接寫3
再去尋求過程 當他是1+1時候 此時後設可以幫助3這答案成立
可以說1+1+1=3 獲者說1+1=3-1
這樣子的假設有助於我們在創作上的靈活度與可能性的存在
孫老師當日的評論的確有一種"不能討論性"的意思
當日最重的一句話就是總結論時所説
:「來我這邊應徵,像一般大學生我會給他們2萬2,
如果像你們這種的研究生我只會給你們1萬8千。」
物價上漲了A~至少要加2千阿!
哈哈!真廉價阿!
多謝你的鼓勵阿(有空去誠品翻一下我的作品集阿!免費的呵呵捧個場)
共勉之吧!
而且我倒不認為設計或創作有天份可言
基本上畫100次同樣的一張畫,第1次跟第101次絕對會差異
;或者同樣的寫1次文章跟寫100次的厚度也會不同
量多質變應該是說們組上的座右銘吧
"寬厚隨和"
呵呵第一次有人這樣說!害我都不知道如何回應了= =
假設也比較像是我们在做創作的意涵
或者說一般方法論者或過程美學者
講求都是"實事求是";相較於我們就像是"虛事求是 轉為實"
當中的兩個實意義上是不一樣的
這樣說好了 方法論就像是 數學公式1+1=2它是有循序漸進的得到答案
而我們呢!在沒有公式之前就假設答案直接寫3
再去尋求過程 當他是1+1時候 此時後設可以幫助3這答案成立
可以說1+1+1=3 獲者說1+1=3-1
這樣子的假設有助於我們在創作上的靈活度與可能性的存在
孫老師當日的評論的確有一種"不能討論性"的意思
當日最重的一句話就是總結論時所説
:「來我這邊應徵,像一般大學生我會給他們2萬2,
如果像你們這種的研究生我只會給你們1萬8千。」
物價上漲了A~至少要加2千阿!
哈哈!真廉價阿!
多謝你的鼓勵阿(有空去誠品翻一下我的作品集阿!免費的呵呵捧個場)
共勉之吧!
-

chaos47 - 文章: 20
- 註冊時間: 2008 9月 13 (週六) 3:27 pm
以上文約分成兩種態度
一種似乎肯定這些建築作品的形成方法...
另一種批評這種東西不切實際天馬行空...
接著
我來談談我個人的意見與看法
第一
我想這是一個程度還不錯 試著用腦袋做抽象性的邏輯思考的人 花工夫做建築設計
注意: 所謂抽象性邏輯思考....是有邏輯的 完全的邏輯
不然 哲學不就通通沒有邏輯 通通像做愛一樣一個感覺叫好爽而已?
人家認真想事情 就別在旁邊叫著說你的結構咧? 你的廁所咧? 你的糞管咧? 在哪? 我看不到阿?
今天換作是我正在認真思考 或者認真與人討論設計思想時
跑來一個老建築師硬在那邊說我功能有問題 結構有問題....我絕對會立刻用髒話問候他媽
真的 我發過誓 我一定要罵到那老建築師哭著說要告我為止!
那種人念建築系就為了考照 考照為了窮翻身 真不知羞恥
爛環境就是他們搞出來的
第二
另一個角度,若真的這麼愛深深地思索著建築中的真理,放洋去那幾間名校找人狠狠K你會比較過癮~
第三
當我在誠品翻到這本書時,......發現我對歐巴馬、巴菲特的自傳更有興趣
這是在我過去幾年已經看過好多好多的設計相關書籍以後...人會變的
現在 我喜歡暢銷書
一種似乎肯定這些建築作品的形成方法...
另一種批評這種東西不切實際天馬行空...
接著
我來談談我個人的意見與看法
第一
我想這是一個程度還不錯 試著用腦袋做抽象性的邏輯思考的人 花工夫做建築設計
注意: 所謂抽象性邏輯思考....是有邏輯的 完全的邏輯
不然 哲學不就通通沒有邏輯 通通像做愛一樣一個感覺叫好爽而已?
人家認真想事情 就別在旁邊叫著說你的結構咧? 你的廁所咧? 你的糞管咧? 在哪? 我看不到阿?
今天換作是我正在認真思考 或者認真與人討論設計思想時
跑來一個老建築師硬在那邊說我功能有問題 結構有問題....我絕對會立刻用髒話問候他媽
真的 我發過誓 我一定要罵到那老建築師哭著說要告我為止!
那種人念建築系就為了考照 考照為了窮翻身 真不知羞恥
爛環境就是他們搞出來的
第二
另一個角度,若真的這麼愛深深地思索著建築中的真理,放洋去那幾間名校找人狠狠K你會比較過癮~
第三
當我在誠品翻到這本書時,......發現我對歐巴馬、巴菲特的自傳更有興趣
這是在我過去幾年已經看過好多好多的設計相關書籍以後...人會變的
現在 我喜歡暢銷書
最後由 sunglin 於 2009 2月 06 (週五) 12:03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1 次。
- sunglin
- 文章: 202
- 註冊時間: 2008 10月 29 (週三) 12:59 pm
chaos47 寫:孫老師當日的評論的確有一種"不能討論性"的意思
當日最重的一句話就是總結論時所説
:「來我這邊應徵,像一般大學生我會給他們2萬2,
如果像你們這種的研究生我只會給你們1萬8千。」
物價上漲了A~至少要加2千阿!
哈哈!真廉價阿!
對於價碼 我有深深的體會
管他1.8 2.2萬
通通乘以三 還是不會致富!
多磨練實務經驗 和 多做思考訓練
都是成功所必備
大部分人天生沒有世界級的才氣 無法在成長過程中就隱約瞭解那麼多道理
所以才得練習~
這一切都是練習的過程 練不好就平庸過一輩子 既然要平庸....2.2萬和5萬...差飯好不好吃而已
管你領多少錢都得互相尊重不是嗎
要不然發錢的大爺不就秋翻了
- sunglin
- 文章: 202
- 註冊時間: 2008 10月 29 (週三) 12:59 pm
llmj 寫:綜合上面先進們的敘述,倒是建議在書名部分,可以加上「紙上」建築,或是其他名詞,來表達你是想談的創作過程,不是真的建築。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建築觀,我的建築觀是:美學與機能要能均衡,滿足人的需求。還有網頁最上面標題所示。
當然,你不需要說服我,我尊重你們的創作,不過倒是很想瞭解如同mysmalllamb所說:「你們的建築藝術創作如何能對建築實務產生貢獻呢? 如何真實改善空間品質呢? 或是有其它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爽就好?」
各位在看待建築設計個過程裡 或許太專注於執行的那一面
如果說 這些建築藝術創作 對於建築實務有什麼貢獻?
我想 就是在思考的過程
建築設計從案子開始就已經充滿整個過程 直到完工驗收
每一個階段 即使是跟業主的溝通 都可以說是 設計的一環
所以 專心於最前面階段設計思考的朋友
也是提供我們在實務界打混 而沒有時間整理設計思緒的這些人
有點喘息的空間 有點靈感的刺激
建築的分工可以很細緻
每一個步驟都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如同HSM所說
只要是在學校階段所做的設計 都不算是一建築物
對於實務界來說那些也都只能算是概念設計的階段
距離落實 還有很大一條路要走
今天 這位仁兄努力的在這一過程當中
並且呈現給大家
並不代表他沒有執行後段的能力
我們也不需要去猜測
只要欣賞此一作品所努力的內容
我想對我們彼此都會有收穫
對於所謂建築實務 也會有幫助的
以上
- HHM
- 文章: 52
- 註冊時間: 2009 3月 13 (週五) 11:55 am
很遺憾,我並不認同這位黃先生與該校學長的看法。
我舉伊東豐雄的仙台媒體中心為例。

為了克服樓版剪穿的問題,而在樓版與大型鋼管束交接的地方用了什麼樣的構造,是這個設計案能夠成立的重點。換個角度來說,是由樓版剪穿問題開始發展出這個概念的說法也不算過分。
另外再舉神奈川工科大學的technology workshop為例:


這許多的柱子中,有某些比例的柱子是設計為「拉力柱」的。有「拉力柱」這種東西?還有,柱子這麼細不會發生挫屈嗎?據建築師說,他為了決定柱子的平面配置,對於這個workshop的空間先進行了數百次的排列。這些問題正是設計案發想的起點啊。
再舉我最喜愛的(我是老套,沒辦法)落水山莊來說,可說是當時劃時代的先進設計。為了讓建築物能夠懸挑在瀑布之上,建築師用了什麼樣的構造與結構手段才達成,而當時這樣規模的鋼筋混凝土懸臂結構設計有多麼異端,相信學過建築史的各位一定都相當了解。如果當初萊特是抱著黃先生這種態度的話,或許現在那個瀑布上出現的是一家格子趣?
也就是說,沒有對於建築構造與力學的了解,是不可能出現這些設計案的發想的。為了克服現實生活上的問題而展開的創意才有真正的力量。在還沒有面對現實問題之前先逃避,認為那是在設計案後期才要面對的「骯髒東西」的這種態度,我覺得教出這樣學生的教育系統是有很大問題的。
我舉伊東豐雄的仙台媒體中心為例。

為了克服樓版剪穿的問題,而在樓版與大型鋼管束交接的地方用了什麼樣的構造,是這個設計案能夠成立的重點。換個角度來說,是由樓版剪穿問題開始發展出這個概念的說法也不算過分。
另外再舉神奈川工科大學的technology workshop為例:


這許多的柱子中,有某些比例的柱子是設計為「拉力柱」的。有「拉力柱」這種東西?還有,柱子這麼細不會發生挫屈嗎?據建築師說,他為了決定柱子的平面配置,對於這個workshop的空間先進行了數百次的排列。這些問題正是設計案發想的起點啊。
再舉我最喜愛的(我是老套,沒辦法)落水山莊來說,可說是當時劃時代的先進設計。為了讓建築物能夠懸挑在瀑布之上,建築師用了什麼樣的構造與結構手段才達成,而當時這樣規模的鋼筋混凝土懸臂結構設計有多麼異端,相信學過建築史的各位一定都相當了解。如果當初萊特是抱著黃先生這種態度的話,或許現在那個瀑布上出現的是一家格子趣?
也就是說,沒有對於建築構造與力學的了解,是不可能出現這些設計案的發想的。為了克服現實生活上的問題而展開的創意才有真正的力量。在還沒有面對現實問題之前先逃避,認為那是在設計案後期才要面對的「骯髒東西」的這種態度,我覺得教出這樣學生的教育系統是有很大問題的。
最後由 shaoyen 於 2009 5月 04 (週一) 9:30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1 次。
- shaoyen
- 文章: 378
- 註冊時間: 2008 1月 18 (週五) 5:21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