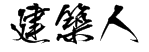[轉載]給黃聲遠也是給建築人的一些話by孫德鴻
3 篇文章
• 第 1 頁 (共 1 頁)
[轉載]給黃聲遠也是給建築人的一些話by孫德
贊助商連結
給黃聲遠也是給建築人的一些話
接下來呢? 2006/08/18 12:13
http://tw.myblog.yahoo.com/fleishmannfa ... &l=f&fid=7
從礁溪戶政及衛生所談黃聲遠 孫德鴻 2006.1.30
一年多近二年前的一個傍晚,就在台灣建築獎評審團的座車從宜蘭返回台北的路上,黃聲遠的礁溪戶政及衛生所突然出現在新省道的路邊,對於這幾秒鐘的驚鴻一瞥,眾人先是一陣錯愕,繼而是一片質疑的聲音,不過質疑很快就結束,所有人的焦點沒多久就轉移到首獎究竟該頒給誰的爭執裡,在一片熱烈的討論聲中,我心中始終沒離開那個突然出現在路邊,盡是矯揉做作之姿的建築物,心中最大的疑惑是:黃聲遠怎麼了?
這樣的疑惑兩年來未曾稍減,尤其是當丟丟銅計畫出現在宜蘭車站前方之後,整件事情變得越來越詭異,而那個向來盡力保存古老巷弄、賣命維護小城尺度的黃聲遠身影則變得越來越模糊,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何在全力保護宜蘭車站附近每個不管值不值得保存的歷史建築的同時,卻放手讓站前漫步大道的超大樹型鋼棚用超出宜蘭車站小尖塔一倍高度以及前糧食局倉庫N倍高度的酷斯拉姿態出現?導致整個車站前方呈現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讓多年的努力毀於一旦,彷彿在經過長期的巷戰後,小尺度與地方原味開始節節敗退,最後在地形開闊處展開形式之役的最後一戰,形式主義領導的鋼鐵巨獸終於取得優勢佔領了宜蘭車站?還是說黃聲遠終於丟開小尺度與零散分割的堅持,開始與當年美國西部的造鎮英雄或是費城William Penn的巨大身影靠攏了嗎?
黃聲遠的作品向來如連續劇(當然「意難忘」除外)一般,如果單看其中一集可能無法窺其全貌,將近兩年未見,懷著巨大疑惑,我決定親自造訪黃聲遠以及他的礁溪戶政及衛生所(以下簡稱戶衛所)。
戶衛所坐落於礁溪新省道旁,整個平面呈L型配置,前窄後寬,左側是中華電信公司,右側則是台灣長老教會與附設幼稚園,四周還有幾條古老而狹小的巷弄,這些巷弄不但是早期住民經常利用的貿易要徑,也是今日附近學生上下課必經的通道,善於利用都市涵構的黃聲遠當然沒錯過這些重要元素,在考慮配置的同時,亦積極參與相關公共決策,促成了周邊巷弄的保留,而將開放空間留設於幼稚園側則是另一個典型的黃氏決策,兩塊基地的開放空間合併之後的空間效果相當有趣,除了傳統的基地界線徹底消失外,對於社區功能的強化更有著極為正面的影響,不管是從現場幼稚園學生以及附近小學生的使用狀況,或者是從都市涵構的填補與強化角度而言,此案的配置是成功的。
然而就建築設計邏輯而言,這絕對是一棟極具爭議性的房子。
黃聲遠企圖以「無名 無形」謙稱這個建築,可是姿態的強迫性卻早已推翻一切,整棟房子從裡到外,紛雜的設計手法隨處可見,雖然在設計完整度與施工整合上確實下了不少功夫,對於材質的選擇與掌握也較之前洗練,只是無論如何無法讓人忽略其主宰周邊視覺環境的企圖,這棟歪斜不正的公共建築在「無名 無形」的標籤下,不但無法隱入週遭的環境中,反而成為宜蘭另一個醒目的觀光地點,過往行人完全無法忽略其獨特性與突兀性,整個扭曲傾斜的姿態也遠比西堤社福館醒目作態,在都市涵構中的各種努力依舊被過度的建築操弄打敗,像是一顆很有想法的齟齒,不情願的待在一整排面無表情的牙齒當中,雖稱無形,可是終究有形,而且還很佔眼睛,真正無名的反倒是那些賦與實際機能的公家機關。
就設計邏輯而言,雖然自稱無意遵循任何邏輯,但是黃聲遠喜好的碎塊原則依舊清晰可辨,自礁溪竹林安養院以降的層層脫開方式仍然強烈的主導整體氛圍,而各樓層時而出現的小小植栽穴也確實讓人有種身在一樓的感覺,加上富於野趣的植栽設計,這種打破樓層限制讓各樓層的風景自成一格的努力確實非常具有黃氏色彩,只是對於黃聲遠自稱的故事線索:「蒸騰的煙與遠方的山」而言,如此以隨性手法鋪陳的設計安排畢竟未竟全功,例如一樓的白色的煙柱並未讓人真的產生溫泉的聯想,舖貼於四樓結構版底的復古柚子型小口磚也因為距離過遠,根本無法在尺度上與過去的溫泉浴池產生聯想,四稜砂岩的利用本來極具創意,但是僅出現在某些柱面作材料樣品般的的展示,而非順著登山的邏輯或是山的紋理去安排,委實非常可惜,經過實際走訪後,只能說本案的實際使用效果與登山的意境相比仍有相當的距離,除了上述一些未能掌握的機會外,黃氏若真有意貫徹設計意志,對於一些樓梯的細節自然不應有菁英化的傾向,雖然鋼筋為主的欄杆作法已經比一般常見的不鏽鋼材質更能搭配本案風貌,也確實增添不少趣味,但是如此激烈好像要說些什麼的歪斜與扭曲卻非因本案而特別設計,而是已經成為黃聲遠近期的標準手法,如火車站前整排散步空間中就處處可見,這樣的無限制沿用反而容易讓人解讀為雜誌看多了或是中了Enrico Miralles的毒所致。
而對於結構的說詞則讓人有點摸不著頭緒,黃聲遠說:「結構本就是自由的。動物有肢、有節,每一個斷面都有效的分出粗細……。」如果拿動植物極具完美邏輯與力學意涵的各種結構設計來談,我們絕對可以發現其結構是嚴謹的,只有創意才是自由的,在這棟建築裡也許創意是自由的,但結構則是隨性的或是有意識的亂整,致使整個建築出現許多類似補強手法或仿違章建築手法,若說這是向結構乖乖主義宣戰或是與矯飾主義靠攏還比較貼切,拿動植物的嚴謹結構來與本案相比就顯得過於牽強。
儘管本案有一些無法澄清的心態與邏輯爭議,然而黃聲遠仍舊創造了好些的令人讚嘆的空間,例如每個樓梯空間所呈現的趣味性讓人驚訝,不管是上樓還是下樓,視線轉折時出現的空間變化確實是處理的不錯的地方,即便在同一樓層,視野也因為地坪的高低起伏而充滿變化,而不甘願平坦、非得到處折來折去的平台空間雖然只是某種流行,但在小小使用者充斥其間後,竟也出現許多使用上的童趣,而類似的童趣在整個建築裡無目的無限制的展開且串連在一起,如同童玩節的延伸,有時還與某些機能結合成另類的空間型態,我認為這絕對是某種無法忽略的成就,尤其是自省道入口向下通往衛生所的樓梯,幾乎是宜蘭隨處可見通往灌溉溝渠旁邊生活場域階梯的完整再現,相信會令熟悉宜蘭的人會心一笑。
有一位國內從事品牌塑造(Branding)工作多年的朋友曾說:不論你經不經營你的形象,你都會有一個形象。這句話正好說明了黃氏處境的矛盾予尷尬之處,不管黃聲遠在不在乎,他與他的作品都會產生某種形象,也許是一種用心耕耘、努力玩耍、不問收穫的感覺,但是在有意或無意之間,黃聲遠似乎開始走上另一條路,如果我們把時間調回五、六年前,逐漸獲得宜蘭官方與民間信任的黃聲遠對於每個案件的掌握顯然較為全面,儘管許多手法引起爭議,但是他對於宜蘭地方的經營卻是有目共睹的,只接宜蘭案子、喜穿藍白拖鞋的黃聲遠確實做了很多一般建築師不做的事情,他有著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也有著探詢所有鄉間小徑的雅興,對於小城鎮固有價值的保留絕對不只是略盡綿薄而已,也因此過去對於黃聲遠的作品,一般評論者均不願過度苛責其手法的成熟度,像是員山忠烈祠突兀的加蓋物,以及礁溪鎮公所後方的玻璃盒子,儘管多慾熱鬧而不精簡,但其造型底下的出發點可能是美麗的,原本應該產生的負面評價,最後也會被黃聲遠所作過的的社會付出所平息。只是一旦事務所的心態開始出走,開始做出如丟丟銅或是礁溪文化館(黃說:幸好只是草案階段)這類英雄尺度而且不符合宜蘭天空標準的公共建築後,黃氏最大的悲哀可能不是被廣泛討論,也不是被指責,而是不再被談起,人們只會依稀記得那個理想色彩濃郁的短頭髮,不會也不再認得現在或是未來的黃聲遠,因為台灣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建築師了,他們並沒有在建築專業外付出額外的社會參與,可能是他們對公共事務的興致不高,但也極有可能是他們的設計野心僅止於建築其形,不像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或是柯比意(Le Corbusier)般有著改變城市的巨大興趣,黃聲遠心中的真正意圖無法探知,但至少當初他所選擇的是一條嚴峻而孤獨的道路,因為不太有人願意走,所以一旦投身其中之後要擁有光環是既容易又辛苦的,只是一旦小有成果就開始搖擺,甚至加入為數眾多的流行教派行列時,其況可想而知。所以討論黃聲遠的作品絕對不是對或錯的分析,就建築的投入性而言,這裡談的只是88分或90分的問題,比起台灣一堆不到30分而無法談論的建築師而言,黃聲遠代表的比較像是某種“社會建築家”的道德標準,而檢驗黃聲遠的作品,則比較像是檢驗我們自己心中通往最後淨土的那扇門,當世俗的灰塵淹沒來時路,當那扇門終於無法尋覓,當我們無法保住最後的理想性格時,我們會害怕他人也失去。
黃聲遠的事務所終究不是一人事務所,由個位數到二十幾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無法完善管制的情事必然每天發生,年輕一代的從業人員帶著理想來到宜蘭,在瀏覽各種雜誌上各種流行的建築成果之餘,這些建築同胞對於任何可能的設計機會必然也會產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自我期許,於是在管理上有能無力的無奈情緒中或是給年輕人一點空間的多方權衡之下,過度稚嫩缺乏歷練的手法就會不停出現,或許是勢之所趨,或許是黃氏默許,可是自詡為游擊隊的黃聲遠可能忘記一件事,那個為世人以及黃聲遠所景仰的真正游擊隊員Che Ernesto Guevara,其真正災難的開始是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後出任政府高官,不用多說這絕對不是Che的真正心志,因此在許多觀念上開始與卡斯楚漸行漸遠,數年後再度隱入中南美洲叢林致力於革命輸出、協助貧窮農民對抗美國主導的傀儡政府機器也許才是其真正本性所在,黃聲遠在宜蘭搧風點火之後,知名度也跟著水漲船高,再加上各次得獎的光環,也許讓他逐漸忘記當初的出發點,一旦開始住在這種成就之中,或是事務所同事開始向台灣一些愛好使用所謂精英語彙的建築工作者的心態看齊後,則革命早就結束,黃聲遠如果真的自認是永遠的游擊隊,應該對下面這段描述不會陌生:
他不談論自己、從不抱怨,他不是生產者、居無定所,日子是辛苦的,醫藥永遠不夠,在四處遊走的生活中,他嚴格限制他的同袍:要請求、不要掠奪,人民依靠他們提供的某種希望而奮鬥,他們則依靠人民的接應而存活,他不打正規戰,只加入零星戰鬥,牽制與消耗是他的最大目的,友軍壯大甚至攻城掠地時,他也不會加入共享成果,革命多年,即便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他也僅會在荒遠的一角遙祝朋友,經過短暫的心靈祝賀儀式之後,率領殘部,向叢林深處再度隱沒。
那麼黃聲遠要往何處去?
加入建築人討論區粉絲團
- L-archi
- 文章: 3134
- 註冊時間: 2007 11月 10 (週六) 10:59 am
- 來自: 台灣
對於孫老師的一番話,心中甚為激動,
不是在意於孫老師對於黃建築師的任何批評或期待。
因為那與我無關,我在意的是孫老師文章背後要告訴
從事建築實務的建築人對於這個城市,這塊土地所應
投入的責任與情感,事務所經營的壓力往往讓我們迷
失在工作與金錢的誘惑中,我們往往忘記了那起初投
入建築這個職場所宣誓的理想與抱負,每一個城市都
需要許多有良知願意付出的建築人來投入,否則百年
之後(甚至幾十年後),我們或許會讓我們的子孫恥
笑我們的無知與不認真。
再次感謝孫老師的金玉良言,至少讓我個人又重新省
思那起初的理想與抱負,莫辜負了上帝所賞賜給我們
的恩賜!
不是在意於孫老師對於黃建築師的任何批評或期待。
因為那與我無關,我在意的是孫老師文章背後要告訴
從事建築實務的建築人對於這個城市,這塊土地所應
投入的責任與情感,事務所經營的壓力往往讓我們迷
失在工作與金錢的誘惑中,我們往往忘記了那起初投
入建築這個職場所宣誓的理想與抱負,每一個城市都
需要許多有良知願意付出的建築人來投入,否則百年
之後(甚至幾十年後),我們或許會讓我們的子孫恥
笑我們的無知與不認真。
再次感謝孫老師的金玉良言,至少讓我個人又重新省
思那起初的理想與抱負,莫辜負了上帝所賞賜給我們
的恩賜!
- kctou
- 文章: 7
- 註冊時間: 2008 4月 27 (週日) 7:52 am
- 來自: 上帝祝福之地
3 篇文章
• 第 1 頁 (共 1 頁)